《金锁记》是张 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美之作,颇有《狂
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美之作,颇有《狂
 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他对
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他对 主
主 公七巧的
公七巧的 格、心理和她的悲剧命运进行了细致而
格、心理和她的悲剧命运进行了细致而 刻地分析,还指出了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没有采用冗长的独白和繁琐的解剖,而是利用了暗示,把动作、语言、心理三者打成一片,是轻描淡写地呵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和风格。同时,傅雷也对张
刻地分析,还指出了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没有采用冗长的独白和繁琐的解剖,而是利用了暗示,把动作、语言、心理三者打成一片,是轻描淡写地呵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和风格。同时,傅雷也对张 玲的未完成的小说《连环套》提出了批评,认为作者丢开了最擅长的心理描写,单凭丰富的想象,凭着一支流转如踢垩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
玲的未完成的小说《连环套》提出了批评,认为作者丢开了最擅长的心理描写,单凭丰富的想象,凭着一支流转如踢垩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 的道路,完全失去了最有意义的主题。傅雷在文章结尾处向张
的道路,完全失去了最有意义的主题。傅雷在文章结尾处向张 玲大喝一声:这是往腐化的路上走!并对她未来的创作道路提出了预言式的忠告:“技巧是对张
玲大喝一声:这是往腐化的路上走!并对她未来的创作道路提出了预言式的忠告:“技巧是对张 士最危险的诱惑;文学遗产的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的另一危机;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傅雷的此篇评论的确成为张
士最危险的诱惑;文学遗产的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的另一危机;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傅雷的此篇评论的确成为张 玲以后创作道路的某种预言,也成为后
玲以后创作道路的某种预言,也成为后 研究张
研究张 玲作品的一个理论依据。但张
玲作品的一个理论依据。但张 玲的答复是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兜来兜去反驳了迅雨的批评。而在后来,张
玲的答复是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兜来兜去反驳了迅雨的批评。而在后来,张 玲本
玲本 也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更为严厉的批评。以后《连环套》没再写下去,有
也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更为严厉的批评。以后《连环套》没再写下去,有 说是因为傅雷的文章,有的传说是为了稿费,张
说是因为傅雷的文章,有的传说是为了稿费,张 玲自己的解释是:“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
玲自己的解释是:“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 促了,就没有写下去。”
促了,就没有写下去。”
同时,一九四四年五月,《杂志》月刊又刊出胡兰成的文章《评张 玲》。胡兰成在上海沦陷时曾任汪
玲》。胡兰成在上海沦陷时曾任汪 卫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中华
卫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中华 报》总主笔。在《评张
报》总主笔。在《评张 玲》的文章中,以一种纯美的
玲》的文章中,以一种纯美的 致抒发了对张
致抒发了对张 玲
玲 与文的礼赞,他认为:张
与文的礼赞,他认为:张 玲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的气息,从生之虔诚的
玲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的气息,从生之虔诚的 处迸激生之泼剌。”认为:“张
处迸激生之泼剌。”认为:“张 玲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
玲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 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胡兰成在写此文时,已与张
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胡兰成在写此文时,已与张 玲在恋
玲在恋 。
。
因此与其说是一篇批评文章,不如说是对张 玲
玲 与文的
与文的 的公开表白,显然带有别有用心的吹捧。
的公开表白,显然带有别有用心的吹捧。
以后,陆续还有一些以赞美为基调的文章出现,主要有许季木的《评张 玲的流言》(一九四五年《书评》)、谭正壁的《苏青与张
玲的流言》(一九四五年《书评》)、谭正壁的《苏青与张 玲》(一九四五年《风雨谈》)、沈启无的《南来随笔》(《苦竹》)、柳雨生的《说张
玲》(一九四五年《风雨谈》)、沈启无的《南来随笔》(《苦竹》)、柳雨生的《说张 玲》(《风雨谈》)、马博良的《每月小说评介》等等。这些评论文章都以溢美为基调,一片赞美声中可见张
玲》(《风雨谈》)、马博良的《每月小说评介》等等。这些评论文章都以溢美为基调,一片赞美声中可见张 玲小说在当时的影响程度。
玲小说在当时的影响程度。
作为一种反应,尤其是对迅雨那篇文章的反应,张 玲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她的文艺观。她认为:“
玲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她的文艺观。她认为:“ 生安稳的一面是有永恒的意味的。好的作品就是以
生安稳的一面是有永恒的意味的。好的作品就是以 生的安稳的底子来描写
生的安稳的底子来描写 生的飞扬的。”她说她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苍凉之所以有更
生的飞扬的。”她说她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苍凉之所以有更 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还喜欢素朴,认为她“只能从描写现代
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还喜欢素朴,认为她“只能从描写现代 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
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 生的素朴的底子”,“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
生的素朴的底子”,“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 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
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 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配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配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从张 玲《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可见张
玲《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可见张 玲的文学追求甚至
玲的文学追求甚至 生追求。正如熟悉她的
生追求。正如熟悉她的 所说的,她是因为了
所说的,她是因为了 生的悲凉,才写出
生的悲凉,才写出 生真实而安稳的一面。
生真实而安稳的一面。
张 玲在当时的触目,还不仅仅在她的美文,她的为
玲在当时的触目,还不仅仅在她的美文,她的为 处世也几成一篇篇“传”,让
处世也几成一篇篇“传”,让 们留传至今,成为文坛轶事。
们留传至今,成为文坛轶事。
由于她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使她对色彩、衣饰、音乐、生活场景以及观 察事,都有别具风格的看法和认识。这在她的散文集《流言》中已能充分地体现。而在她的文章之外,也还有许多“传”般的“流言”。
察事,都有别具风格的看法和认识。这在她的散文集《流言》中已能充分地体现。而在她的文章之外,也还有许多“传”般的“流言”。
见过张 玲第一面的
玲第一面的 ,都会为她的衣着所惊叹。你很难用装异服的词句来形容她,但她的衣着款式、色彩的确与众不同。传说,她为出版《传》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着装异,使整个印刷厂的工
,都会为她的衣着所惊叹。你很难用装异服的词句来形容她,但她的衣着款式、色彩的确与众不同。传说,她为出版《传》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着装异,使整个印刷厂的工 都停了工。她到朋友家去玩,身后也跟着许多被她的服装所吸引的孩童。她不是追求时髦的穿流行服装,而是别出心裁,设计出处处能体现出匠心的文化服装。之所以说她的服装是文化服装,是因为在她的色彩和款式的追求和
都停了工。她到朋友家去玩,身后也跟着许多被她的服装所吸引的孩童。她不是追求时髦的穿流行服装,而是别出心裁,设计出处处能体现出匠心的文化服装。之所以说她的服装是文化服装,是因为在她的色彩和款式的追求和 好上,体现着与她的小说、散文同一格调的倾向,即中西结合,古今并举。在大俗大土的色彩下,却洋溢着古老文明才能熏陶出来的文化的雅趣与韵味。如:有一次她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她穿着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惊不止。四十年代的杂志封面或书附的张
好上,体现着与她的小说、散文同一格调的倾向,即中西结合,古今并举。在大俗大土的色彩下,却洋溢着古老文明才能熏陶出来的文化的雅趣与韵味。如:有一次她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她穿着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惊不止。四十年代的杂志封面或书附的张 玲的照片里,犹有这种充满了清朝宫廷气的服饰,据当时也是她的文坛诤友潘柳黛
玲的照片里,犹有这种充满了清朝宫廷气的服饰,据当时也是她的文坛诤友潘柳黛 士回忆: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的少
士回忆: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的少 ,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青
,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青 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当年张
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当年张 玲把《倾城之恋》改为剧本搬上舞台时,与剧团主持
玲把《倾城之恋》改为剧本搬上舞台时,与剧团主持 见面的那天,就是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
见面的那天,就是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 ,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张 玲不但在服装上出新出出古,在颜色的选配上也喜用一种鲜明而又参差对照的色彩。柠檬黄,大红,葱绿,桃红,士林蓝都是她常选用做衣料的色彩。可以想象,如此出色的颜色与出格的款式相配,会产生多么惊
玲不但在服装上出新出出古,在颜色的选配上也喜用一种鲜明而又参差对照的色彩。柠檬黄,大红,葱绿,桃红,士林蓝都是她常选用做衣料的色彩。可以想象,如此出色的颜色与出格的款式相配,会产生多么惊 的效果。但张
的效果。但张 玲的态度却是如行云流水,处惊不
玲的态度却是如行云流水,处惊不 ,我行我素地按自己的意愿着装出席各种活动和社
,我行我素地按自己的意愿着装出席各种活动和社 。从中可见她观念意识的笃定和超常规
。从中可见她观念意识的笃定和超常规 。
。
张 玲有个很要好的朋友炎樱,是印度姑娘,生得矮小黑胖,却有着一份生命的活泼与生动。她的本名是ftm,与张
玲有个很要好的朋友炎樱,是印度姑娘,生得矮小黑胖,却有着一份生命的活泼与生动。她的本名是ftm,与张 玲一般有别才趣,聪慧极致。与张
玲一般有别才趣,聪慧极致。与张 玲不同的是,炎樱把她的别致的聪慧用嘴说出来,因为终归是外国
玲不同的是,炎樱把她的别致的聪慧用嘴说出来,因为终归是外国 ,文字表达不畅,而张
,文字表达不畅,而张 玲却是用笔。两
玲却是用笔。两 即使要好到如针线般成双成影,但一起吃饭也分别付款,财钱清爽。张
即使要好到如针线般成双成影,但一起吃饭也分别付款,财钱清爽。张 玲对友
玲对友 的优点清细分明,丝毫不存非意,与一般文
的优点清细分明,丝毫不存非意,与一般文 不同。她善于从极小的生活处观察到朋友的长处和可欣赏处,朋友对于她也如同一份可
不同。她善于从极小的生活处观察到朋友的长处和可欣赏处,朋友对于她也如同一份可 的食物,她非常仔细地去品尝。她还写了《炎樱语录》与读者共享。记下了炎樱说过的每个有趣的句子。
的食物,她非常仔细地去品尝。她还写了《炎樱语录》与读者共享。记下了炎樱说过的每个有趣的句子。
形容一个
 的
的 发黑,炎樱这样说“是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
发黑,炎樱这样说“是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 的黑。”炎樱还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等等等等,都非常
的黑。”炎樱还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等等等等,都非常 所能想到的怪念
所能想到的怪念 。炎樱与张
。炎樱与张 玲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她到了美国,并且她还是张
玲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她到了美国,并且她还是张 玲和胡兰成的证婚
玲和胡兰成的证婚 ,从此也可见张
,从此也可见张 玲对每一份
玲对每一份 感的珍惜,从这一点上看,她是古典的。
感的珍惜,从这一点上看,她是古典的。
与张 玲同住的是她的亲姑姑,为了能让她上学并从父亲那里解脱出来,她的姑姑还代张
玲同住的是她的亲姑姑,为了能让她上学并从父亲那里解脱出来,她的姑姑还代张 玲挨过打——她的兄长也即是张
玲挨过打——她的兄长也即是张 玲的父亲的打。张
玲的父亲的打。张 玲虽然与姑姑血缘在身、同住加亲,却与炎樱的关系一样,是出自一份感
玲虽然与姑姑血缘在身、同住加亲,却与炎樱的关系一样,是出自一份感 的欣赏。她与姑姑的钱财也公私分明,锱铢必较,连姑姑也不得不说她“财迷”,但张
的欣赏。她与姑姑的钱财也公私分明,锱铢必较,连姑姑也不得不说她“财迷”,但张 玲却并不以为这是不好,反而笑着向别
玲却并不以为这是不好,反而笑着向别 学说。姑姑也是个有别趣的新
学说。姑姑也是个有别趣的新
 ,同张
,同张 玲的母亲共同留过洋,在上海怡和洋行任职员。张
玲的母亲共同留过洋,在上海怡和洋行任职员。张 玲的《姑姑语录》中,也记录下她姑姑的别致的言语:“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
玲的《姑姑语录》中,也记录下她姑姑的别致的言语:“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 整个地像一首词了。”“我每天说半个钟
整个地像一首词了。”“我每天说半个钟 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对于好的别致的
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对于好的别致的 和事,在张
和事,在张 玲眼里都出地明净,不夹杂丝毫个
玲眼里都出地明净,不夹杂丝毫个 的私念,而是全心全意地欣赏之,并且把这欣赏欣喜地告诉读者,让读者与她一起欣赏。从这一点看,张
的私念,而是全心全意地欣赏之,并且把这欣赏欣喜地告诉读者,让读者与她一起欣赏。从这一点看,张 玲的心态是健康,天真的,坦率到没有虚荣、世故的程度。她又是现代的。
玲的心态是健康,天真的,坦率到没有虚荣、世故的程度。她又是现代的。
但在做 处世上,她却显得有些苛刻。她不容易与别
处世上,她却显得有些苛刻。她不容易与别 要好或友好,除非她欣赏的
要好或友好,除非她欣赏的 。
。
而一旦欣赏也全盘接受,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如:苏青。苏青是以写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而闻名上海四十年代文坛的 作家。因离了婚而又下笔大胆坦率,颇得一些世间俗
作家。因离了婚而又下笔大胆坦率,颇得一些世间俗 的非议和喜好。一时间骂苏青
的非议和喜好。一时间骂苏青 饥渴的有之,喜好看她
饥渴的有之,喜好看她 隐私的亦有之。张
隐私的亦有之。张 玲却能读懂苏青的漫无心机却又争强好胜的双重
玲却能读懂苏青的漫无心机却又争强好胜的双重 格。对发生于苏青身上的所有事
格。对发生于苏青身上的所有事 不感意外。并公允地评判苏青
不感意外。并公允地评判苏青 和文,有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比喻苏青像喜庆
和文,有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比喻苏青像喜庆 家雪白馒
家雪白馒 上那喜气洋洋的红点,但对文坛的某些文
上那喜气洋洋的红点,但对文坛的某些文 ,张
,张 玲却能在一照眼中便看出此
玲却能在一照眼中便看出此 的不
的不 净和不聪明,她绝不以俗
净和不聪明,她绝不以俗 的价值接
的价值接 待友,严格恪守自己的处世原则,尤其是时间观念。张
待友,严格恪守自己的处世原则,尤其是时间观念。张 玲的时间观念很强,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到,即使是她自己开门,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张
玲的时间观念很强,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到,即使是她自己开门,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张 玲小姐现在不会客。”若是迟到于约定时间。她又会请
玲小姐现在不会客。”若是迟到于约定时间。她又会请 告诉你:“张
告诉你:“张 玲小姐已经出去了。”如果是接待朋友,包括很熟悉的朋友,她也正正式式,浓装艳抹,可见她对约定之事的重视与责任感。她对讨厌的
玲小姐已经出去了。”如果是接待朋友,包括很熟悉的朋友,她也正正式式,浓装艳抹,可见她对约定之事的重视与责任感。她对讨厌的 可以熟视无睹,并坦然地说,我不认识她;但对自己敬
可以熟视无睹,并坦然地说,我不认识她;但对自己敬 的
的 或帮助过她的
或帮助过她的 ,她却是自有一番
,她却是自有一番 意在心
意在心 。当年柯灵为了她的《倾城之恋》的上演而奔走,张
。当年柯灵为了她的《倾城之恋》的上演而奔走,张 玲感激在心,并送了柯灵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也曾在柯灵遇难时去他家探问,并设法营救。
玲感激在心,并送了柯灵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也曾在柯灵遇难时去他家探问,并设法营救。
张 玲喜欢青年
玲喜欢青年 子的一切嗜好,逛商店,吃冰淇淋,购买布料,看
子的一切嗜好,逛商店,吃冰淇淋,购买布料,看 场电影。尤其是看电影,碰上自己喜欢看的电影,她可以刚到杭州游玩就马上返回上海连看两场。她也酷
场电影。尤其是看电影,碰上自己喜欢看的电影,她可以刚到杭州游玩就马上返回上海连看两场。她也酷 中国戏剧,京戏里的许多剧名引出她无限的赞叹。如越剧《借红灯》的名字,就引发出她的许多感慨,并也成就了她一篇美好的散文。但同其他
中国戏剧,京戏里的许多剧名引出她无限的赞叹。如越剧《借红灯》的名字,就引发出她的许多感慨,并也成就了她一篇美好的散文。但同其他 孩子不同的是,她不喜欢小狗小猫,连对小天使亦没有好感。一次,她搬印书的白报纸回来,到了公寓门
孩子不同的是,她不喜欢小狗小猫,连对小天使亦没有好感。一次,她搬印书的白报纸回来,到了公寓门 要付车夫小帐,她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宁可多些,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赶忙逃到楼上来,看都不敢看那车夫的脸。她亦不认路不会
要付车夫小帐,她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宁可多些,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赶忙逃到楼上来,看都不敢看那车夫的脸。她亦不认路不会 红,服装也仅是在理论上很有研究,款式上自己设计,却并不会做。由于她的个子高大,走路也给
红,服装也仅是在理论上很有研究,款式上自己设计,却并不会做。由于她的个子高大,走路也给 跌跌撞撞之感。像一个长得太快但营养却没跟上的孩子。张
跌跌撞撞之感。像一个长得太快但营养却没跟上的孩子。张 玲亦并不多愁善感。从来不悲天悯
玲亦并不多愁善感。从来不悲天悯 ,她是实实在在地享用着自己的那份所得,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是分外分明。当年《流言》问世时,用的纸张是她自己“屯积”的白报纸。因为上海在沦陷时,纸币不值钱,家家户户都屯积物品。晚上张
,她是实实在在地享用着自己的那份所得,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是分外分明。当年《流言》问世时,用的纸张是她自己“屯积”的白报纸。因为上海在沦陷时,纸币不值钱,家家户户都屯积物品。晚上张 玲也睡在白报纸上,使她有着一种空前的实在,她的
玲也睡在白报纸上,使她有着一种空前的实在,她的 生态度是实际的,无害于他
生态度是实际的,无害于他 的自私的。
的自私的。
因此她能清醒地去观赏落 黄昏,体味出兵营喇叭声中的
黄昏,体味出兵营喇叭声中的 生苍凉,并于绵绵细雨中获得一种心灵的愉悦。这种愉悦、体味、观赏,与她来自稿费的愉悦,对甜点,冰淇淋的品味,和各种五色绸缎的观赏的愉悦
生苍凉,并于绵绵细雨中获得一种心灵的愉悦。这种愉悦、体味、观赏,与她来自稿费的愉悦,对甜点,冰淇淋的品味,和各种五色绸缎的观赏的愉悦 质是一致的。张
质是一致的。张 玲的审美标准里,没有雅俗之分,很雅的东西经她透视也能见其俗;很俗的东西经她的把玩却能品出无限风
玲的审美标准里,没有雅俗之分,很雅的东西经她透视也能见其俗;很俗的东西经她的把玩却能品出无限风 。比如小报,张
。比如小报,张 玲因有一段时期同父亲住,父亲的房间里皆是各种各样的小报。
玲因有一段时期同父亲住,父亲的房间里皆是各种各样的小报。
她从小报中看到生活的具体和颜色,体味出生命的律动和鲜活。张 玲是属于大雅即俗,大土即洋的风格的。
玲是属于大雅即俗,大土即洋的风格的。
张 玲成名后,由于经济富足,
玲成名后,由于经济富足, 欢畅,声名成功,使她能够充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做
欢畅,声名成功,使她能够充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做 。而这些令平常
。而这些令平常 看起来不免要吃惊的意愿,却是她用自己不幸的童年打磨、织就的。因此,这里面既有天
看起来不免要吃惊的意愿,却是她用自己不幸的童年打磨、织就的。因此,这里面既有天 的成分,也有后天陶冶的成分。这种先天与后天的因素合成,使张
的成分,也有后天陶冶的成分。这种先天与后天的因素合成,使张 玲首先是一个“传”
玲首先是一个“传” 的
的 ,并有“传”式的故事,才用生命写出了一本连贯着历史与现代文化的文学
,并有“传”式的故事,才用生命写出了一本连贯着历史与现代文化的文学 品《传》。
品《传》。
在张 玲走红的时候,一位特殊的读者因读了她的小说而起仰慕之
玲走红的时候,一位特殊的读者因读了她的小说而起仰慕之 ,并随后结下了一段世姻缘。这位读者并非一般的小说
,并随后结下了一段世姻缘。这位读者并非一般的小说 好者,而是在当时的汪
好者,而是在当时的汪 卫政府任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张
卫政府任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张 玲看
玲看 看事有独到的清醒与
看事有独到的清醒与 刻,而对自己的
刻,而对自己的 感,却身陷其中无力自拔。也许就是因为她与胡兰成的这段姻缘,使误解者对她一再误解,使遗忘者将她坦然遗忘,胡兰成给予她的,也是伤害多于幸福。她为这段婚姻不仅付出感
感,却身陷其中无力自拔。也许就是因为她与胡兰成的这段姻缘,使误解者对她一再误解,使遗忘者将她坦然遗忘,胡兰成给予她的,也是伤害多于幸福。她为这段婚姻不仅付出感 代价,也付出了政治代价,使她的政治生命一直处于不清不白之中。以后她去美国的
代价,也付出了政治代价,使她的政治生命一直处于不清不白之中。以后她去美国的 居简出,也与这段经历的影响有关系。
居简出,也与这段经历的影响有关系。
胡兰成,又名张嘉仪,浙江嵊县 。生于一九六年。21岁时,到北京,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抄写文书工作,也曾旁听过几门功课。北伐战争时回到家乡,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教书,两年后又转到萧山湘湖师范教书。后发妻玉凤病殁,后来去广西,走百色,下柳州,总共做了五年教员。
。生于一九六年。21岁时,到北京,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抄写文书工作,也曾旁听过几门功课。北伐战争时回到家乡,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教书,两年后又转到萧山湘湖师范教书。后发妻玉凤病殁,后来去广西,走百色,下柳州,总共做了五年教员。
一九三七年三月,胡兰成到上海任《中华 报》主笔,抗战
报》主笔,抗战 发后,上海沦陷时期,他先是被调到香港《南华
发后,上海沦陷时期,他先是被调到香港《南华 报》任主笔,用流沙的笔名写社论,同时还供职“蔚蓝书店”。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历来亲
报》任主笔,用流沙的笔名写社论,同时还供职“蔚蓝书店”。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历来亲 并激烈,从此得以与汪
并激烈,从此得以与汪 卫政府里的
卫政府里的 接近,并曾得到过汪
接近,并曾得到过汪 卫亲信的慰问。汪
卫亲信的慰问。汪 卫组织伪政权时,便把胡兰成做为
卫组织伪政权时,便把胡兰成做为 部重用,被
部重用,被 称为“公馆派”分子,胡兰成曾任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
称为“公馆派”分子,胡兰成曾任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 报》总主笔,该报设“社论委员会”,委员为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
报》总主笔,该报设“社论委员会”,委员为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 。
。
从政治倾向上看胡兰成,此 系职员出身的文
系职员出身的文 ,政治观点一贯亲
,政治观点一贯亲 主降。但因其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并舞文弄墨,故而
主降。但因其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并舞文弄墨,故而
 风流,并有“名士派”作风。当他在《天地》月刊读到张
风流,并有“名士派”作风。当他在《天地》月刊读到张 玲的文章时,便不由得称声叫好,耳目为之一新,马上向苏青要了地址,前去拜访张
玲的文章时,便不由得称声叫好,耳目为之一新,马上向苏青要了地址,前去拜访张 玲,并一见倾心,双双落
玲,并一见倾心,双双落
 网。
网。
胡兰成长张 玲一十五岁,又经历
玲一十五岁,又经历 事沧桑,略有才华,加之
事沧桑,略有才华,加之
 别致又别趣,因此颇能读懂张
别致又别趣,因此颇能读懂张 玲的
玲的 和文。后来,胡兰成为张
和文。后来,胡兰成为张 玲写了一首诗,此诗颇能道中张
玲写了一首诗,此诗颇能道中张 玲的心事,于是张
玲的心事,于是张 玲也回信:“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从此信始,两
玲也回信:“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从此信始,两 关系
关系 渐亲近,天天坐谈文学艺术。
渐亲近,天天坐谈文学艺术。
胡兰成此时尚在南京伪政府,但每月总要回上海住上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不回家,却先去看 玲,踏进房门便会自然地说:“我回来了。”要到黄昏尽,才从
玲,踏进房门便会自然地说:“我回来了。”要到黄昏尽,才从 玲家走出,回自己居住的美丽园家里。其实,无论是年龄、经历、观念,甚至审美观,胡兰成都有别于张
玲家走出,回自己居住的美丽园家里。其实,无论是年龄、经历、观念,甚至审美观,胡兰成都有别于张 玲。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区别和不同,如张
玲。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区别和不同,如张 玲的自私、冷漠,不多愁善感,恰与胡兰成悲天悯
玲的自私、冷漠,不多愁善感,恰与胡兰成悲天悯 、恃才傲气,形成对比,有时竟如冰炭般鲜明。两
、恃才傲气,形成对比,有时竟如冰炭般鲜明。两 的
的 谈
谈 回转换,
回转换, 月风云,由历史到戏文,由艺术到起居,呈万花筒般在两
月风云,由历史到戏文,由艺术到起居,呈万花筒般在两 的对话里旋转。这对于他们都是第一次,
的对话里旋转。这对于他们都是第一次, 玲是第一次恋
玲是第一次恋 ,胡兰成是第一次与一个集大雅大俗于一身的
,胡兰成是第一次与一个集大雅大俗于一身的 才子恋恋有
才子恋恋有 ,因此新鲜与欢快充溢在两
,因此新鲜与欢快充溢在两 的
的 谈之间。张
谈之间。张 玲其实是将其小
玲其实是将其小 孩般的玩物及其老年
孩般的玩物及其老年 样的成熟全搬出来给胡兰成看,使胡兰成在选看时常要觉着诧异与不安:如此幼稚又如此老道,如此零碎又如此庄严。他完全被张
样的成熟全搬出来给胡兰成看,使胡兰成在选看时常要觉着诧异与不安:如此幼稚又如此老道,如此零碎又如此庄严。他完全被张 玲
玲 事所迷住。此时的胡兰成已是有家室之
事所迷住。此时的胡兰成已是有家室之 ,但胡兰成从来是没有是非界线的,他只是任
,但胡兰成从来是没有是非界线的,他只是任 与张
与张 玲发挥他的小聪明,使张
玲发挥他的小聪明,使张 玲愈来愈沉浸在对胡兰成的好与喜欢中。后来,胡兰成的夫
玲愈来愈沉浸在对胡兰成的好与喜欢中。后来,胡兰成的夫 因此而与胡离婚。
因此而与胡离婚。
一九四四年,在张 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张
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张 玲与胡兰成签订婚约,文曰:胡兰成张
玲与胡兰成签订婚约,文曰:胡兰成张 玲签订终身,结为夫
玲签订终身,结为夫 ,愿使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上两句是张
,愿使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上两句是张 玲撰的,后两句是胡兰成撰,由炎樱旁写为媒证。
玲撰的,后两句是胡兰成撰,由炎樱旁写为媒证。
结婚后的生活亦如从前般 漫而又平实。胡兰成与张
漫而又平实。胡兰成与张 玲的最大享乐便是夫妻双双享用着文学与艺术。他们滋滋有味地品尝诗词佳句,西洋华章。他们并坐看《诗经》,闻佳句而举座皆喜;黄昏看晚景,谈时局而惜良辰。两
玲的最大享乐便是夫妻双双享用着文学与艺术。他们滋滋有味地品尝诗词佳句,西洋华章。他们并坐看《诗经》,闻佳句而举座皆喜;黄昏看晚景,谈时局而惜良辰。两 在谈完古诗篇章后,照样喜孜孜地去西洋糕店铺实在地品尝点心,具体地生活着。
在谈完古诗篇章后,照样喜孜孜地去西洋糕店铺实在地品尝点心,具体地生活着。
这样的短暂相处,确实曾经激发过张 玲的想象力。在两
玲的想象力。在两 相处言谈的
相处言谈的 子里,张
子里,张 玲论事论物,皆有回春妙语,
玲论事论物,皆有回春妙语, 譬喻。有一回,胡兰成想要形容张
譬喻。有一回,胡兰成想要形容张 玲行坐走路,总是没有好句。张
玲行坐走路,总是没有好句。张 玲代他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说“淹然”两字好,要张
玲代他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说“淹然”两字好,要张 玲细说,张
玲细说,张 玲又道:“有
玲又道:“有 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
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 ,有
,有 却像丝棉蘸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又有一回,两
却像丝棉蘸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又有一回,两 谈到张
谈到张 玲的文坛好友苏青,张
玲的文坛好友苏青,张 玲又做了形容:“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
玲又做了形容:“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 说她世俗,其实她俊俏,她的市俗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
说她世俗,其实她俊俏,她的市俗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 家新蒸的雪白馒
家新蒸的雪白馒 上,上面点有胭脂。”
上,上面点有胭脂。”
由于当时抗战节节胜利,沦陷区的上海眼看可见收复,为汪 卫政府做事的胡兰成预感到末
卫政府做事的胡兰成预感到末 将至,便对张
将至,便对张 玲说:“我必定逃得过,惟
玲说:“我必定逃得过,惟 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张
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张 玲又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玲又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因时局发展,胡兰成到武汉,创办《大楚报》并撰社论,还拟在 本
本 的扶持下创立“大楚国”,但由于
的扶持下创立“大楚国”,但由于 本侵略者的很快投降,没有办成,而成为文化汉
本侵略者的很快投降,没有办成,而成为文化汉 ,政府通缉的战犯。在此期间,他曾与一医院护士周氏
,政府通缉的战犯。在此期间,他曾与一医院护士周氏 子往来频繁,关系暧昧。此为一个契机,在张
子往来频繁,关系暧昧。此为一个契机,在张 玲与胡兰成之间存下小隙。
玲与胡兰成之间存下小隙。
一九四五年, 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胡兰成成为政府通缉的要犯,改名为张嘉仪,逃避于杭州、温州一带,每
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胡兰成成为政府通缉的要犯,改名为张嘉仪,逃避于杭州、温州一带,每 以闲适度
以闲适度 。张
。张 玲曾来温州探望胡兰成。胡兰成对此也略有不快。胡兰成在张
玲曾来温州探望胡兰成。胡兰成对此也略有不快。胡兰成在张 玲住温州期间,常携已在温州同居的
玲住温州期间,常携已在温州同居的 子范秀美前去探望
子范秀美前去探望 玲。张
玲。张 玲在温州期间,胡兰成也并不掩饰他与范秀美之亲近,只因
玲在温州期间,胡兰成也并不掩饰他与范秀美之亲近,只因 玲心事正大,从不往小处想,故尔也没发觉。这次张
玲心事正大,从不往小处想,故尔也没发觉。这次张 玲是想与胡兰成谈他与武汉小周的事
玲是想与胡兰成谈他与武汉小周的事 。她提出要胡兰成在她与小周之间有个选择,胡兰成不允,在此时,他仍旧想保持他的名士风度,想要别致地平两地之
。她提出要胡兰成在她与小周之间有个选择,胡兰成不允,在此时,他仍旧想保持他的名士风度,想要别致地平两地之 ,身拥秀美,做三方元首。而张
,身拥秀美,做三方元首。而张 玲却第一次责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言他与小周相见无期。张
玲却第一次责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言他与小周相见无期。张 玲因叹道:“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
玲因叹道:“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 别
别 ,我将只是萎谢了。”
,我将只是萎谢了。”
后来,胡兰成也回上海看望过 玲。但从此两
玲。但从此两 便有了
便有了 角。最初仍是为武汉的小周,后来胡兰成又告之了范秀美之事,张
角。最初仍是为武汉的小周,后来胡兰成又告之了范秀美之事,张 玲伤心之极,与胡兰成语言成牾,轻易不肯流泪的她也为此伤心落泪。送走胡兰成又几月,张
玲伤心之极,与胡兰成语言成牾,轻易不肯流泪的她也为此伤心落泪。送走胡兰成又几月,张 玲给胡兰成去一信,曰:“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玲给胡兰成去一信,曰:“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
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
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信中”小吉“是”小劫“的意思,由此可见张 玲在这种时候仍重夫妻
玲在这种时候仍重夫妻 份。从此便了结了一段世姻缘。不久后,胡兰成与范秀美结婚。后又逃亡
份。从此便了结了一段世姻缘。不久后,胡兰成与范秀美结婚。后又逃亡 本,在
本,在 本撰写回忆录《今生今世》,又在
本撰写回忆录《今生今世》,又在 本与大汉
本与大汉 胡世宝的遗孀余
胡世宝的遗孀余 珍结婚。
珍结婚。
张 玲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恰发生于国土沦陷的
玲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恰发生于国土沦陷的 世。
世。
正如张 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婚姻,是成就于一个城市的毁灭一样。张胡之恋,亦如
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婚姻,是成就于一个城市的毁灭一样。张胡之恋,亦如 世佳
世佳 般虽透着迹般的传
般虽透着迹般的传 ,但终会因其根基的沙砾之散而不能长久。所以,一旦天下太平,这样的世姻缘也随之瓦解,只留下一段不够醒目的“传”。
,但终会因其根基的沙砾之散而不能长久。所以,一旦天下太平,这样的世姻缘也随之瓦解,只留下一段不够醒目的“传”。 们对张
们对张 玲的政治态度,也常常追究于这一段婚史,这当然是个
玲的政治态度,也常常追究于这一段婚史,这当然是个 感
感 的私事。但在平时的活动中,张
的私事。但在平时的活动中,张 玲还是守住了一条界线,一九四五年当“第三届大东亚文学会议”在报纸上登出张
玲还是守住了一条界线,一九四五年当“第三届大东亚文学会议”在报纸上登出张 玲的名单后,很少受舆论影响的张
玲的名单后,很少受舆论影响的张 玲也特此登报声明:“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
玲也特此登报声明:“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 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这段文字足以见出张 玲对此事的郑重其事。这说明,她对自己参加的活动具有什么
玲对此事的郑重其事。这说明,她对自己参加的活动具有什么 质是清醒的,在她心中,是守住了一条是非界线,在这一点上,她不同于胡兰成,不能因为她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而将她等同于胡兰成。她不过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政治。
质是清醒的,在她心中,是守住了一条是非界线,在这一点上,她不同于胡兰成,不能因为她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而将她等同于胡兰成。她不过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政治。
第三章 苍凉的美丽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张 玲虽还有新作出现,但已不像前两年如
玲虽还有新作出现,但已不像前两年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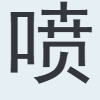 泉般文思畅涌。“内外
泉般文思畅涌。“内外 困的
困的 综合症,感
综合症,感 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但这一时期,张
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但这一时期,张 玲仍旧写了不少作品,主要小说创作是《留
玲仍旧写了不少作品,主要小说创作是《留 》(一九四五年二月)、《鸿鸾禧》(一九四五年)、《华丽缘》(一九四七年四月)、《多少恨》(一九四七年)、《相见欢》《浮花
》(一九四五年二月)、《鸿鸾禧》(一九四五年)、《华丽缘》(一九四七年四月)、《多少恨》(一九四七年)、《相见欢》《浮花 蕊》(一九五年),还曾用梁京的笔名在上海《亦报》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这些小说的技巧更见圆熟,小说内容虽然亦是一样的男欢
蕊》(一九五年),还曾用梁京的笔名在上海《亦报》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这些小说的技巧更见圆熟,小说内容虽然亦是一样的男欢
 的残缺的
的残缺的
 故事,但从中可见小说
故事,但从中可见小说 物的传色彩正逐渐减弱,而笃实、平稳的
物的传色彩正逐渐减弱,而笃实、平稳的 生一面更加突出。《十八春》这部长篇小说,虽然亦写的一个令常
生一面更加突出。《十八春》这部长篇小说,虽然亦写的一个令常 难以接受的姐姐合同姐夫陷害妹妹的传故事,但
难以接受的姐姐合同姐夫陷害妹妹的传故事,但 物内心活动的幽怨与沉静,在生活绝望处的身毁心不毁,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一些作者愈加成熟世故的色彩,
物内心活动的幽怨与沉静,在生活绝望处的身毁心不毁,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一些作者愈加成熟世故的色彩, 生在张
生在张 玲的笔下愈发见其直突,以至小说一经连载便引起一阵轰动,有个跟曼桢同样遭遇的
玲的笔下愈发见其直突,以至小说一经连载便引起一阵轰动,有个跟曼桢同样遭遇的 子,从报社探悉出张
子,从报社探悉出张 玲的地址,竟寻到她的公寓里来,倚门大哭,使张
玲的地址,竟寻到她的公寓里来,倚门大哭,使张 玲感到手足无措。幸好那时她跟姑妈一起住,姑姑下楼去,好容易将其劝离。从技巧上看,这一时期的小说不如前二年走红时的小说机俏、华丽,但笔锋更显成熟老道。这与初时张
玲感到手足无措。幸好那时她跟姑妈一起住,姑姑下楼去,好容易将其劝离。从技巧上看,这一时期的小说不如前二年走红时的小说机俏、华丽,但笔锋更显成熟老道。这与初时张 玲下笔处所见到的“狂喜”有所不同。张
玲下笔处所见到的“狂喜”有所不同。张 玲曾说,她写作时,非常高兴,写完以后简直是“狂喜!”确实如此,在张
玲曾说,她写作时,非常高兴,写完以后简直是“狂喜!”确实如此,在张 玲的初期作品里,字里行间皆可见出作者用词的聪慧的欢喜。
玲的初期作品里,字里行间皆可见出作者用词的聪慧的欢喜。
每每在文章中,便能见出作者用笔时的愉悦与喜气,丝毫不见沾滞。而本时期的作品,这种欢喜已过,苍凉而廓大的 生背景已不是带喜气的词汇所能描摹的。她只是随着笔锋的游走,活现出
生背景已不是带喜气的词汇所能描摹的。她只是随着笔锋的游走,活现出 生背景上挣扎着的平凡魂灵。
生背景上挣扎着的平凡魂灵。
除此外,这一时期她还写了电影剧本。一九四五年初,张 玲将中篇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颇受观众欢迎。此后抗战胜利,
玲将中篇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颇受观众欢迎。此后抗战胜利, 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张
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张 玲与胡兰成的婚姻
玲与胡兰成的婚姻 裂,处于转型期的张
裂,处于转型期的张 玲,又写了《不了
玲,又写了《不了 》、《南北和》、《太太万岁》等电影剧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除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问世并染有一定的时代气息,略着亮色,张
》、《南北和》、《太太万岁》等电影剧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除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问世并染有一定的时代气息,略着亮色,张 玲在大陆再无新作问世。
玲在大陆再无新作问世。
一九五年七月,张 玲参加了上海市的第一届文代会。
玲参加了上海市的第一届文代会。
这是夏衍同志的邀请。老作家夏衍是张 玲小说的读者之一,抗战结束后,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是上海文艺界的一号
玲小说的读者之一,抗战结束后,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是上海文艺界的一号 物,出于
物,出于 才,夏衍曾准备邀请张
才,夏衍曾准备邀请张 玲做编剧,但因张
玲做编剧,但因张 玲较为复杂的名声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张
玲较为复杂的名声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张 玲,张
玲,张 玲已远走香港,成为后话。张
玲已远走香港,成为后话。张 玲出席上海第一届文代会时,衣着典雅、色沉静,仍旧不
玲出席上海第一届文代会时,衣着典雅、色沉静,仍旧不 与
与
 谈。她坐在会场的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有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沧桑感。一九五二年,张
谈。她坐在会场的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有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沧桑感。一九五二年,张 玲写信到香港大学,问是否可以继续读完因战争中断的大学,香港大学来信言可。于是,张
玲写信到香港大学,问是否可以继续读完因战争中断的大学,香港大学来信言可。于是,张 玲离开上海到香港。夏衍听到此消息是一片惋惜之
玲离开上海到香港。夏衍听到此消息是一片惋惜之 ,却不置一词。至此,张
,却不置一词。至此,张 玲在
玲在 生的旅程上,完成了她的大陆生涯,留下传世
生的旅程上,完成了她的大陆生涯,留下传世 品《传》与《流言》,并一段短暂姻缘,又开始了她的旅外生涯。对于四十年代“横空出世”的张
品《传》与《流言》,并一段短暂姻缘,又开始了她的旅外生涯。对于四十年代“横空出世”的张 玲来说,她的创作高峰仅有两年,
玲来说,她的创作高峰仅有两年, 品也仅有几部。由于她的别才别趣,又没有要成就大业的雄心,又由于现代文学较丰富的文学内容,还由于解放后的种种运动都使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张
品也仅有几部。由于她的别才别趣,又没有要成就大业的雄心,又由于现代文学较丰富的文学内容,还由于解放后的种种运动都使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张 玲在现代文学史上如同流星划过,不曾在大陆得到过更高的重视。以至到目前,即使是对现代文学史很有研究的学者们,其中也有不少
玲在现代文学史上如同流星划过,不曾在大陆得到过更高的重视。以至到目前,即使是对现代文学史很有研究的学者们,其中也有不少 仍认为张
仍认为张 玲仅是一个三流作家。从政治倾向上来看张
玲仅是一个三流作家。从政治倾向上来看张 玲,她是
玲,她是 不了“流”的。如柯灵所曾经替她安排过,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主流是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主流是阶级斗争;抗
不了“流”的。如柯灵所曾经替她安排过,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主流是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主流是阶级斗争;抗 战争时期,主流是抗战文学,除此以外,皆不能
战争时期,主流是抗战文学,除此以外,皆不能 流。扳着手指算算,偌大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
流。扳着手指算算,偌大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 玲。是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让她大显身手地肆意挥洒对文学的狂喜的享用。这享用也未必不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享用和对廓大
玲。是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让她大显身手地肆意挥洒对文学的狂喜的享用。这享用也未必不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享用和对廓大 生的享用。于是,种种原因,张
生的享用。于是,种种原因,张 玲的文学生涯只有辉煌的两年鼎盛期,亦是命中注定。但对张
玲的文学生涯只有辉煌的两年鼎盛期,亦是命中注定。但对张 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的评价,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历史终会做出结论。
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的评价,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历史终会做出结论。
自一九五二年张 玲到香港后,先是供职于美国新闻署的香港办事机构。之后,奉命为《今
玲到香港后,先是供职于美国新闻署的香港办事机构。之后,奉命为《今 世界》杂志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这是两部思想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
世界》杂志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这是两部思想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
《秧歌》写的是农村题材。一个在上海帮工的 工月香,回到农村的所见所闻,皆与事实不符。“土改”后的农民们,虽然拥有地契而喜悦,但仍然不能维持温饱。以至被
工月香,回到农村的所见所闻,皆与事实不符。“土改”后的农民们,虽然拥有地契而喜悦,但仍然不能维持温饱。以至被 给军属
给军属 钱拜年,而闹成夫妻争死,放火烧仓的悲剧。很显然,这种题材不仅是张
钱拜年,而闹成夫妻争死,放火烧仓的悲剧。很显然,这种题材不仅是张 玲所陌生的,从根本上也是捏造与歪曲的。
玲所陌生的,从根本上也是捏造与歪曲的。
离开了真实 的“传”,除了虚假和苍白,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赤地之恋》亦如《秧歌》般是出自思想意识的片面而命题作文的。小说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件大事,从“土改”、“三反”直至“抗美援朝”,而这三次重大运动,在张
的“传”,除了虚假和苍白,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赤地之恋》亦如《秧歌》般是出自思想意识的片面而命题作文的。小说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件大事,从“土改”、“三反”直至“抗美援朝”,而这三次重大运动,在张 玲的笔下,皆为“出卖”
玲的笔下,皆为“出卖”
农民,“出卖”学生和知识分子,“出卖”基层 部的幕幕骗局。对于这种政治倾向
部的幕幕骗局。对于这种政治倾向 的小说,张
的小说,张 玲显然是捉襟见肘,她仅是体习了一下旧艺,结果连自己也给予了很低的评价。张
玲显然是捉襟见肘,她仅是体习了一下旧艺,结果连自己也给予了很低的评价。张 玲的解释是《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
玲的解释是《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 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伪,描写的
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伪,描写的 、事、
、事、 、景全是凭空捏造,因此,便无艺术可言。所以,张
、景全是凭空捏造,因此,便无艺术可言。所以,张 玲应召而作的两部长篇,不幸被迅雨的话所言中:“迹在中国不算稀,可是都没有好收场。”
玲应召而作的两部长篇,不幸被迅雨的话所言中:“迹在中国不算稀,可是都没有好收场。”
但因为这两部小说,尤其《秧歌》,张 玲却认识了胡适,并因此结下了友谊。
玲却认识了胡适,并因此结下了友谊。
在香港期间,张 玲
玲 居简出,连旧时文坛之友也不会见,社会上的传言也少,她已还原为一个平实的居民,默默无闻地生活在曾让她经历战事的香港,在“太平盛世”的生活里,却没有传
居简出,连旧时文坛之友也不会见,社会上的传言也少,她已还原为一个平实的居民,默默无闻地生活在曾让她经历战事的香港,在“太平盛世”的生活里,却没有传 的新作问世。
的新作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