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北京的那一年,诗 们都在谈论着海子。同年春天,这位北大毕业、执教于郊县某学校的赤子诗
们都在谈论着海子。同年春天,这位北大毕业、执教于郊县某学校的赤子诗 刚刚在山海关铁道线上卧轨。从此他的诗篇浸透了血的概念。许多
刚刚在山海关铁道线上卧轨。从此他的诗篇浸透了血的概念。许多 都把他当做这个时代年轻的诗歌大师来看待。据说他死时已两天没吃饭,胃里只有几瓣清香的橘片。又听说他生前一直是处子,甚至没正式谈过恋
都把他当做这个时代年轻的诗歌大师来看待。据说他死时已两天没吃饭,胃里只有几瓣清香的橘片。又听说他生前一直是处子,甚至没正式谈过恋 。这也是一种清洁的
。这也是一种清洁的 吧。可他却写过一首缠绵悱恻的
吧。可他却写过一首缠绵悱恻的 歌《三姐妹》,把自己在不同时期暗恋的三个
歌《三姐妹》,把自己在不同时期暗恋的三个 孩比喻为
孩比喻为 原上的三位
原上的三位 。还有一首在戈壁滩上写的《姐姐》,结尾是“今夜,我不想
。还有一首在戈壁滩上写的《姐姐》,结尾是“今夜,我不想 类,我只想你。”这就是海子,单纯而又丰富。读读他的作品吧,那里面延续着他的心跳与脉搏。可以忍受海子离开我们,但我们无法离开海子的诗——他的抒
类,我只想你。”这就是海子,单纯而又丰富。读读他的作品吧,那里面延续着他的心跳与脉搏。可以忍受海子离开我们,但我们无法离开海子的诗——他的抒 品格独树一帜。
品格独树一帜。
正如贵
 的沙龙是
的沙龙是 黎的传统,北京的诗
黎的传统,北京的诗 们也经常聚会——采用通俗化的称法,叫“饭局”(或许大俗即大雅吧)。但清一色的是男
们也经常聚会——采用通俗化的称法,叫“饭局”(或许大俗即大雅吧)。但清一色的是男 角色。这种崇尚清谈的聚会也就基本上没有
角色。这种崇尚清谈的聚会也就基本上没有 别特征。讲述者与倾听者皆以中
别特征。讲述者与倾听者皆以中 的思想家、哲学家抑或艺术家面貌出现,谈玄论道,力求达观。我通过城市东西南北中的不同饭局结识了诸多有意思的诗
的思想家、哲学家抑或艺术家面貌出现,谈玄论道,力求达观。我通过城市东西南北中的不同饭局结识了诸多有意思的诗 。李大卫就是一位。他曾以笔名“维维”火过一阵子,但忽然不写诗了,改写校旱了。在作家出版社出了部长篇,叫《集梦
。李大卫就是一位。他曾以笔名“维维”火过一阵子,但忽然不写诗了,改写校旱了。在作家出版社出了部长篇,叫《集梦 好者》。书名怪怪的,我一开始差点看成是《集邮
好者》。书名怪怪的,我一开始差点看成是《集邮 好者》了。一字之差,但天壤之别。在文联大楼下艾青题匾的四川菜馆,在座的诗
好者》了。一字之差,但天壤之别。在文联大楼下艾青题匾的四川菜馆,在座的诗 们正从理论上为诗歌争执不休,一位相貌英俊的北京小伙子近乎幼稚地谈起最初对缪斯的憧憬:“我父亲有本雪莱全集,英文版,但是苏联印的,翻开来有种很臭的树胶味,可里面那张铜版作者像给我印象极
们正从理论上为诗歌争执不休,一位相貌英俊的北京小伙子近乎幼稚地谈起最初对缪斯的憧憬:“我父亲有本雪莱全集,英文版,但是苏联印的,翻开来有种很臭的树胶味,可里面那张铜版作者像给我印象极 ——那才叫诗
——那才叫诗 !”他童贞般的感
!”他童贞般的感 令我刮目相看。我模糊地想起自己也看过的雪莱肖像的版画。我凝视着李大卫痴迷的面孔:或许这才是真诗
令我刮目相看。我模糊地想起自己也看过的雪莱肖像的版画。我凝视着李大卫痴迷的面孔:或许这才是真诗 ,本色且本质。评论家张颐武的解说印证了我的看法:“李大卫是一个很有趣的
,本色且本质。评论家张颐武的解说印证了我的看法:“李大卫是一个很有趣的 ,他热衷于各种怪的知识,沉迷在许许多多稀的事件之中,始终是生活旁边的一位冷眼的观察者。他隐居在自己家中,漫游在我们城市的腹地。李大卫的生活是相当另类的……他的
,他热衷于各种怪的知识,沉迷在许许多多稀的事件之中,始终是生活旁边的一位冷眼的观察者。他隐居在自己家中,漫游在我们城市的腹地。李大卫的生活是相当另类的……他的 生立场是间离的,是站在外面去思考的,因为他是一个从书中对
生立场是间离的,是站在外面去思考的,因为他是一个从书中对
 有了很清楚很明晰的了解的
有了很清楚很明晰的了解的 。”他的校旱《集梦
。”他的校旱《集梦 好者》更像是梦游者枕边的一整部蝴蝶标本。他延续着庄子的蝴蝶梦。
好者》更像是梦游者枕边的一整部蝴蝶标本。他延续着庄子的蝴蝶梦。
北京的诗 们中,有乐天派、悲观主义者、演说家、社会名流、
们中,有乐天派、悲观主义者、演说家、社会名流、 莽英雄、江湖术士、梦想家、怀乡症患者,有知识分子也有行为艺术流
莽英雄、江湖术士、梦想家、怀乡症患者,有知识分子也有行为艺术流 汉,有穷
汉,有穷 也有富翁。社会身份或许大相径庭,但他们本质上都是诗
也有富翁。社会身份或许大相径庭,但他们本质上都是诗 。这是他们无法涂改的共
。这是他们无法涂改的共 ——相当于血统。北京应该是出大诗
——相当于血统。北京应该是出大诗 的地方——我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还应谨慎地加上一句: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大诗
的地方——我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还应谨慎地加上一句: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大诗 的话。这样我的分析与判断就合
的话。这样我的分析与判断就合 合理了。在物质与
合理了。在物质与 的天平上,诗
的天平上,诗 这个概念注定倾向于
这个概念注定倾向于 那一端的。但愿物质的势力,不至于使诗
那一端的。但愿物质的势力,不至于使诗 的概念,在时代的掌心失去了重量。
的概念,在时代的掌心失去了重量。
北京诗 ,和外省相比,北京诗
,和外省相比,北京诗 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正如
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正如 黎曾云集过将近半个法国的画家。北京诗
黎曾云集过将近半个法国的画家。北京诗 甲天下。
甲天下。
一星期前,面容瘦削的画家高星邀请我与邹静之等 小聚,席间谈论起北京城里那些曾叱咤风云的诗歌少校们的下落,邹静之随
小聚,席间谈论起北京城里那些曾叱咤风云的诗歌少校们的下落,邹静之随 引用了大仙的一句诗:“外省青年,
引用了大仙的一句诗:“外省青年, 夜兼程,向紫禁城飞奔……”我忽然发觉北京城里城外的诗
夜兼程,向紫禁城飞奔……”我忽然发觉北京城里城外的诗 们还是有些区别的——并不仅仅表现在
们还是有些区别的——并不仅仅表现在 音、相貌等方面。我曾经写过一篇《诗歌地理》:以护城河为界,里面的诗
音、相貌等方面。我曾经写过一篇《诗歌地理》:以护城河为界,里面的诗 青梅煮酒、笑傲江湖,以闲适的态度处理艺术、
青梅煮酒、笑傲江湖,以闲适的态度处理艺术、
 、社
、社 活动与
活动与 际关系;外面的诗
际关系;外面的诗 则缠着绑腿、怀揣手稿,披星戴月奔走在各铁路线上,不时用指南针探测城门的方向……必须承认,无论从政治或文化的角度,北京都作为圆心而存在,作为坐标而存在,构成众多外省诗
则缠着绑腿、怀揣手稿,披星戴月奔走在各铁路线上,不时用指南针探测城门的方向……必须承认,无论从政治或文化的角度,北京都作为圆心而存在,作为坐标而存在,构成众多外省诗 渴望攻克的桥
渴望攻克的桥 堡。北京城里的诗
堡。北京城里的诗 之所以以逸待劳且盛行清谈之风,因为他们天生就坐守在终点站,占据着天时地利,以守为攻。外省的诗
之所以以逸待劳且盛行清谈之风,因为他们天生就坐守在终点站,占据着天时地利,以守为攻。外省的诗 则如过江之鲫,拥挤在中途换乘的无名月台上,这注定他们将选择矛而放弃盾,他们的战略只能是以攻为守。城里的诗
则如过江之鲫,拥挤在中途换乘的无名月台上,这注定他们将选择矛而放弃盾,他们的战略只能是以攻为守。城里的诗 稳坐钓鱼台,好扎堆儿但很明显缺乏流
稳坐钓鱼台,好扎堆儿但很明显缺乏流 意识,每逢春暖花开才萌生踏青的念
意识,每逢春暖花开才萌生踏青的念 ,在郊外转悠一圈又回来了。外面的诗
,在郊外转悠一圈又回来了。外面的诗 则周游列国,逐鹿中原直至踏
则周游列国,逐鹿中原直至踏 铁鞋,离城门仍然一箭之遥——当年李自成的臂力倒是把鸣镝
铁鞋,离城门仍然一箭之遥——当年李自成的臂力倒是把鸣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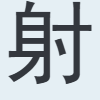 中了故宫的门匾。诗歌界是需要出几个李自成的。
中了故宫的门匾。诗歌界是需要出几个李自成的。
这是否属于另一种围城 结呢?甚至,世纪末的缪斯本身就是一个话、一个名存实亡的空城计呢?真正的尺度掌握在谁的手里?很明显它不应该是一道城门。殿并不是缪斯最确切的住址——如果每一位诗
结呢?甚至,世纪末的缪斯本身就是一个话、一个名存实亡的空城计呢?真正的尺度掌握在谁的手里?很明显它不应该是一道城门。殿并不是缪斯最确切的住址——如果每一位诗 的内心都能供奉一尊缪斯、一尊个
的内心都能供奉一尊缪斯、一尊个 化的保护。
化的保护。
